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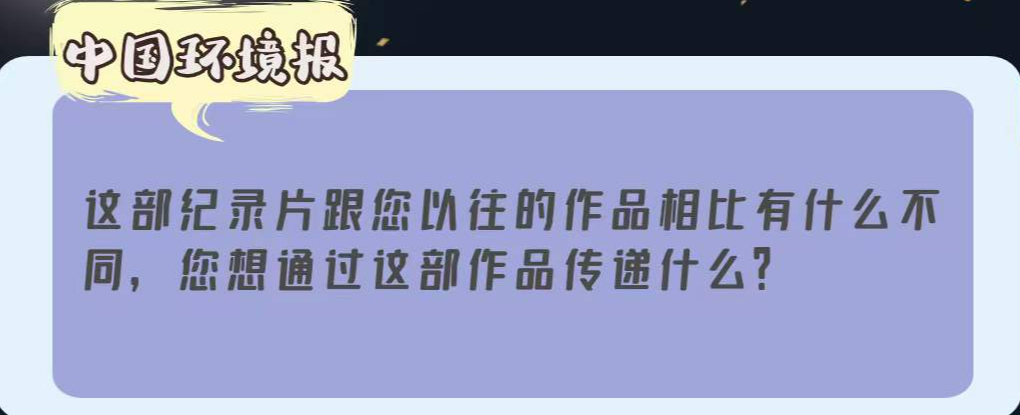
曾海若:其实这跟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没有本质区别。我一直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感兴趣。这次我们拍摄了属于中国的野生动物,选择了特别有代表性,但实际上拍摄起来很难的动物——野牦牛、白海豚、亚洲象和东北虎。它们是分布在中国西北高原、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和东北森林的旗舰物种,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而这4四种动物还能代表中国不同的地貌,它的背后对应的也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代表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关系。
实际上,这部片子比我之前做的任何影片的难度都高。以前拍摄人文故事的片子,人的主动性会强很多,可以与拍摄对象沟通。但是动物就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问野牦牛的想法,只能蹲守在那里,进行细微观察。
所以片子本身也讲了人与动物之间沟通的问题。尤其是白海豚那一集,人类与白海豚的沟通是失效的,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但失效并不是说我们不想沟通,而是沟通的方法不多。因为我们习惯从自己的角度想问题,需要剔除自己的偏见。
其实做动物的片子和做人文的片子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要尊重拍摄对象。尊重的前提是了解,比如说新闻里北上的那十几头亚洲象,以及我们拍摄的那群亚洲象都表现出一定的人象冲突。如果不了解的话,会觉得是大象侵占了人类的地方,但实际上也许人类侵占了它的地方,它们在表达愤怒。纪录片可以提供了解野生动物的窗口。

片子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看来。动物都是自然的使者、自然的晴雨表,或者说它们是大自然设计的最精密的仪器。要想了解大自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了解动物。读懂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读懂了背后的自然。
不同的人去读会获得不同的感受,比如野牦牛那一集里的僧人,可能读到的是神性的东西,而对于牧民来说,他可能读到的是危险。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结合起来,就能稍微接近自然本来的样子。
其实就算没有看这片子(《众神之地》)也没关系,不会有什么损失,也不会影响生活。但是看了之后,对野生动物多一些了解,也许人的生命会开阔一点,原来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一些、丰富一点。不仅仅只是现代化,还有很多虽然古老但也很鲜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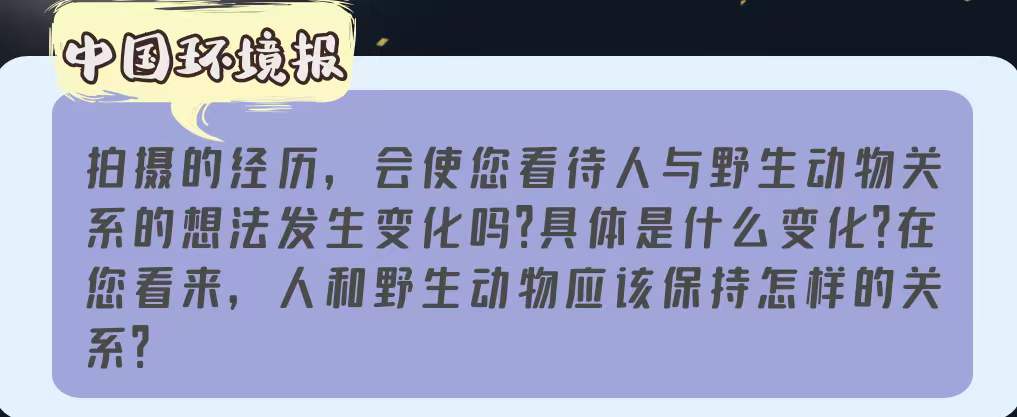
曾海若:拍摄过程中,有很多画面使我印象深刻。 比如野牦牛昆仑的出现,我当时离它大概50米左右的距离,能非常清楚得看到它的眼神,一种非常具有神性的眼神。在野牦牛这一集中,它的眼神是很重要的内容。还有救助白海豚的场景,因为时间来不及分集导演直接拿着手机就去了,在泥地里拍到了当时的画面,正是因为有了那个段落,整个片子才能成型。在看素材时,我还能清晰地听到白海豚的呼吸声。
动物不会说话,很多细节也是稍纵即逝的,如何表现它们喜怒哀乐的情绪,就需要用心体会。 远古时期,一些动物被人类刻在岩石上作为一种图腾崇拜。实际上所有动物身上也许都有着某种神性,这是一种跟自然的联系。这些联系超出日常生活的概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众神之地”指的就是大自然本身。因为大自然就是一个容纳了无数“众神”地方,或者说是创造了很多神迹的地方。

纪录片选择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它们曾经就是被当做自然力量的崇拜对象。但现在这种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人类和它们的关系也改变了。《众神之地》所探讨的就是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但答案也并不唯一。
《众神之地》这个名字其实就代表着一种敬畏。片子里有小野牦牛被人救助,或者老白(白海豚)被救助的情节,但其重点并不是在讲人如何保护动物。实际上这只是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细节而已。人和动物还有很多种关系,有冲突、也有互相协作,也有互相陌生带来的沟通问题。这种关系本身是存在的,但很多时候被忽略了。
在某种程度上,动物其实最需要的并不是人类的保护,而是人类的尊重,把它当做一个与人平等的物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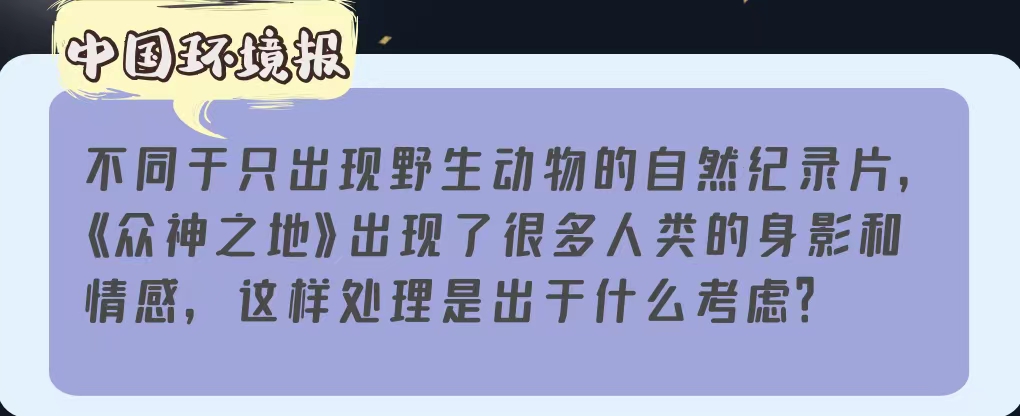
曾海若:我们是人类,不可能变成野牦牛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既然无法脱离人类的视角,那就善用一下,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因为纪录片一方面不能造假,另一方面还需要把50分钟的片子做得好看,具有戏剧性。我和团队能做的就是带着尊重与敬畏接近动物,把感受到的所有东西坦诚地表达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努力接近真相。
动物是一面镜子,通过它们人类可以观察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的山水是无言的,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可以通过维持生态链的平衡来传递大自然是否健康的声音。而这些声音,人类需要听到,也需要尝试着理解。
很多时候,现代人失去了跟自然的连接,也失去了一些能力,人对自然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怎么跟自然相处,其实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我们拍摄时带着敬畏和谦卑,这种情绪和感受传递出来就是答案的一种。

我希望提供给观众这种共鸣,但前提是得做得足够好看。不仅仅只拍摄到动物震撼的画面,还要是把动物的故事和更深的逻辑讲出来。能否表达好这些,其实是我这三年中最焦虑的东西。
三年时间接近这些动物,我现在知道如何把它们拍得更好。只要还有机会,我永远都愿意再去拍摄这类主题的片子。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